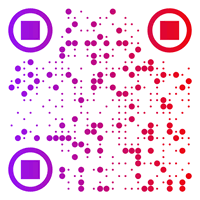“真材实料做面条,由里及外做真人”的两句十四字话语年少的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它几乎成了我整个童年的伴侣。二十四小时追随与身,每日清晨挂于嘴。它是我父亲教我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第一句能够完整默写的话。每天把它装进心里,想小树把水分汲进树干里一样,令人爽朗。从能嗅到这世上的气味时,面香就成了我嗅觉的主角。我的童年里,一直有面香的萦绕。当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所感知时,我才知道,我家是开面坊的。
说是面坊,实则是一块十平米不到的小门面,里面有一个木台子。记忆中的木台子,是棕色和赤色相拼接而成的。岁月在它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可他却不改当年锐气,有力地支撑着一群白扑扑的嫩娃娃。嫩娃娃面似娇嫩,实则硬朗极了!它们长短不一,形态不致。可无论是短的、长的还是细的、宽的,都是给人恍看鲜、白、嫩,细看给人稳、强、韧的感觉。因此在木台子上总是放不久。因为总有大批人马在台前候着长长的队,在嫩娃娃出炉后便一扫而光了。我总是扎着两个麻花辫,踮起脚,一手递出嫩娃娃,一手收进金娃娃。有时忙到衣服上开满晶莹的花,但看到人们拿到嫩娃娃时脸上洋溢的如暖阳的微笑,心中的勉强都释怀了!还有后台父亲忙碌的身影,衣衫早已浸满了汗水。
那时人们常流传出一句话:“不怕生意不火,就怕对手太多”。虽然书文中,常以敌外患者为优,但现实生活中,敌外患者的确能互相激励带来优,但与之同来的也有忧。正在我们生意做得火热之时,对面的那家门店似乎是趁着面热之潮也开张了一家面坊。这样原本一条街只有一个的独宠面坊马上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二者之一,难免拿出来分出胜负。然后一面就是面坊的春天,一面就是面坊的秋天。对面的面坊不仅门面浩大,与之更闪耀的是那镶着红色灯箱、高高挂在门顶上的一个大牌匾,上面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三大字“王面坊”,其中王字的着墨更为浓彩。开张的第一天,锣鼓喧响,张灯结彩,免费凭人领袋儿面。所以那一天,我家门店整个都是安静的,连鸟儿,都在对面的屋檐上欢唱。偶尔有不明现状的人来,见着对面的红火张势,都马不停蹄地冲了过去。因为上面清晰地写着:先到先得,送完即完。
那一天未到黄昏,我就已关上沉重的木门。望着木台子上堆满的嫩娃娃,心中的愁绪像风雨中的雷电,来得更加猛烈。
我一把推开后天的门,头一次看见炉里的熄了,熄了。坐在炉旁的,还有把毛巾搭在肩上的父亲,一种未曾见过却难以诉说的“舒适”。我坐在旁边,一边捣鼓着炉灶里的炭,一边问父亲:“爸,为何我们不弄个牌匾?不然只有木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卖面。”父亲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道:“这面就像你手中的炭一样,将就一个真字,不必在乎外表的。”我看了看手中的炭,好奇地又问:“既然不讲究外表,那怎么将就这个真呢?”父亲拿下肩上的毛巾,细细地给我讲到:“不管炭的大小、形状、颜色,只要一进炉中便可验得是否为真。这面也是一样,一旦下了锅就可以验得是否为真。其他的,什么面坊牌匾呀,面的包装纸纸呀,都是浮华的。”
九岁的我听了好像似懂非懂,像一壶清酒,谈不上有岁月的凛冽感,却好像又有些凉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真”字,也是第一次理解父亲教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那句“真材实料做面条,由里及外做真人”。
第三天的早晨,我等到太阳已经坐到上空时才推开了沉重的木门。没想到外面已经排好了长长的一串人。我看了看对门,只有那日的花残败的在哪儿。父亲出来,脸上也浮出淡淡的笑容。接着叮嘱我千万不要询问对面之事。我轻松地点点头说道:“好,只要你的面是真的,总会有人关注!”父亲听了,转头边走边说道:“不仅面要真,更重要的是人也要真!”听了父亲的话,望着天边似有若无的一抹彩霞,我也笑了。
枯燥无味的日子,因为有面香的纷而美好;平淡无奇的日子,因为有售面的忙碌而精彩。昼与夜的无数更替,面与水的无数搓和,左手与右手的无数交换......童年,就在无数的无数种,像风筝一样,飞走了。现在的前台,已没有当年那个扎着小辫的女孩儿了。她长大了,在父亲教导的“真”中长大了。
十二岁那年,学校在暑假期间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任务:去体验他人的职业,感受他人的生活。我左思右想,也不知道选哪种。当我走进后台,父亲正在忙碌着。我看着他弯下的背,顿时就没了疑问。体验爸爸手中的职业——制面呀!我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只给我说了一句话:“记住‘真材实料做面条,由里及外做真人’就行”。我一口答应了,一股制面势在必得的力量感油然而生。
终于,我体验到了一丝由前台走向后台的自豪感。可我来不及庆祝,因为我在后台时,几乎是到处碰壁。
父亲给了我一围裙,一边语言指导我,一边用行动监督我。首先是调面粉的过程。面粉是爸爸亲自磨的,小麦也是爸爸亲自种的。后山上有块自家的田地,一有空闲时间爸爸就往哪儿跑。他一边望着,一边施肥除草。从春天望到秋天,从绿油油望到金灿灿。那块儿田地,他当宝一样守护着。看着木缸中的面粉,仿佛就看见了父亲在田地上忙碌的身影。调面粉是制面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水和面粉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来调配,多一分水,少一分粉都不行。我在父亲的指导下,两碗半水和一小筐面粉,就调配好了!
接着就是揉面的过程。揉面讲究技巧,讲手法,也讲老实。我看那软软的一堆因水而聚的面团,自以为很好处理,就是双手不断地揉搓它。没想到这水的面粉也不是吃素的,你得反复反复地揉它,才能变成又黏又软又厚实又筋道的面团。我的耐心在揉面团上,几乎很快就消散了。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捶打面条,一锤接一锤。父亲恍然一撇,立马阻止了我的行为。“是揉不是捶,是站不是坐”父亲有些生气地说道。
父亲唱的红脸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深知自己捶面行为的错误。可这面粉,从何而揉?父亲见我的迟钝,立马撸起袖口走了过来。他先把手放进白色的水盆里,用已经从一大块变成一小块的香皂在手上再三涂抹。直到手上都是透明的泡泡时,才露出舒心一笑。然后在清水中再三清洗,直到所有的泡泡都消失了,露出白白嫩嫩的手时才发出爽朗的笑声。忽先忽失的泡泡,每次都能引起父亲忽深忽浅的笑声。每次问其原因,父亲也只是那句:“真手才能做真面!”
紧接着,父亲开始用手揉刚才被我捶打过的那个面团。他先把面团搓中长,然后抓住两端让面团开始在空中与板上跳回旋舞。拉长、重叠......拉长、重叠.......拉长、重叠......无数个跳跃运动后,面团的身材变得十分细腻。然后开始在木板上揉搓、揉搓、揉搓......父亲的手上开始露出了一丝丝青色,与面团交织一起,有些格格不入却又仿佛像注入新鲜的力量,使面团富有生命力,也许这就是父亲的“真”手。
此时父亲的额头已渗慢汗珠。桌上的面团像是从一场长长的美梦中苏醒,变得十分清新,父亲望着面团欣慰地说:“喏,这就是真手揉出的真面!”我看着父亲满带面粉的手,好像进一步又懂得了“真”字。于是我也咬紧牙关,暗下决心一定要以“真”心去揉出真面。
面团揉好了,压平切成细丝,就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考面。所谓烤面,就是将切好的湿面条放在火炉的铁台子上烤。这最关键也是人们最容易疏忽的就是火候。“火候不能过大,进行猛烤;也不能过小,进行微烤,而要用火用得巧!”还未说完,我就已在炉前打起了盹。“梦里的面条又脆又胶又韧又香,我看那人群都已经排到了对面的窗前......”我闻着手中的面条,越闻越香,越闻越香,越闻越香,越闻越......咦?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我恍然地一醒,现实果然很骨感——面,糊了!
我望着那堆黑黢黢的面条,很难想象它们在炉火的炙烤中经历了什么!父亲闻之而来,也是不可思议地望那堆面条。然后双手围起严肃地对我说:“刚才我还以为你在闭目冥思,现在才知道你的真心呢?”我一边挠头一边抓腮,不知所措。父亲见了我没了话语,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做任何事都要真呀!”看着发黑的面条,听着父亲的叮嘱,“真”字,在心中又升了一层次。我包好躺在四周侥幸存活的嫩娃娃些,趁着暮色未临,拿到了前台,回到了前台的位置。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前后台穿梭,从刚开始的制面菜鸟慢慢升级制面新人。当然,与父亲相比,这还只是几招三脚猫功夫。我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因为父亲告诉我,我用了“真”心去对待了面条。
时间一天天地流走,吹过了幽绿的空山谷,飞过了炽热的水田地,走过了金黄的小麦盖,穿过了冰莹的雪世界。一切,都被时间带走了。而在2015年,时间也飘过了我家的小店,我们的店关门了。只见那天父亲站在木门前,一直从正午木讷到黄昏。
年少时期的我,经常在门外看见奔跑、玩耍、自在如风的孩子们,她们的欢声笑语如清澈的银铃声回响在整天街上。我也满生羡慕,经常驻足在窗前痴望一开始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开面坊?直到那天夕阳下,我看父亲的影子忍不住与他对话,把自己拉得很长。我也趁着夕阳之风,问了一个14年想知道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要开面坊?”
只见父亲走向了台阶,坐在了上面。终于波动了嘴:“因为面有灵魂。”
我一惊,面有灵魂?
“从制面到卖面的过程中,所有的真字都是来自于总结。因为面的灵魂——真实,才感染了自己学会了真。”
我也忽然走了过去坐在台阶上,望着着陪了我12年的面坊。突然一点儿都不羡慕当年奔跑的孩子了,因为我觉得此刻的自己,更为幸福。
到现在,我已经是离开面坊的第二年,心中充满难忘、美好与不舍。面坊呀,承载了我的整个童年,也让“真”字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夕阳下,一个父亲摸着女孩子头说:“记住面魂:将究真。”
女孩笑了,心中默默地背了一遍:“真材实料做面条,有里及外做真人。”
火红的晚霞已绚烂地开满天边,好不灿烂!